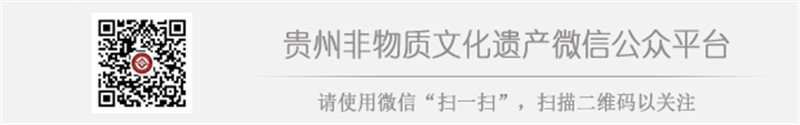【摘要】20世纪初,有关戏曲剧本、道具、脸谱等相关内容的搜集整理与国民教育关系密切。随着社会语境的更迭,传统戏剧的传承及发展始终与时代话语相互缠绕。非遗概念进入中国之后,传统戏剧类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逐渐向资源化、生活化转变。围绕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需要采用资料搜集方法夯实基础;面对“表演”与“传承”问题,遵循生活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及参与式传播等原则,通过“语境”恢复和对“线上民间”的重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形式,运用数字赋能探索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原则;线上民间;数字赋能;发展策略
从戏曲脚本、曲谱、脸谱、服饰的搜集整理到对“讲述情境”“讲述人”的关注,再到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态势。本文从“保护”和“发展”两个角度切入,提出传统戏剧类非遗的保护策略,对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策略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能够推动中国本土特色非遗保护话语的发展,还可为世界非遗保护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传统戏剧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国传统戏剧演化出形态各异的剧种,繁衍生成了种类繁多的声腔。正如戏曲学者刘文峰所指出:“戏剧在形成唱、做、念、打为一体的成熟戏曲形式后,又因受不同民族、不同地区语言、风俗、民间艺术的影响而形成千姿百态的剧种,如京剧、秦腔、梨园戏、藏戏、蒙古戏,等等。”③这一现实造成了戏剧资料搜集的繁难。19世纪中后期,在“文明等级论”的影响下,持变革观念者开始对中国既有之文化资源进行重估,借戏剧资源以应对国内渐趋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希冀将它们改造为唤醒民族精神的催化剂。1916年,《京师教育报》第27期刊载的《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议决戏曲脚本蒐集案》一文中谈及“吾国戏曲种类极繁,一种之中名目极多,即以北京现所通行之二簧一种而论,名目之多,几至不可计极。其他尚有昆腔、秦腔、高腔等类。其剧目更难胜数”,想要搜集“戏曲脚本”,但却由于伶人知识水平的不足和传承方式的特殊性而遇到颇多困难④。
这里对戏曲脚本的搜集整理实际上带有中国古代“采风”思想的底色,在搜集过程中“重文本”,更多以建立资料总藏为主旨。这一时期对戏曲的搜集整理工作,立足于国民观念的塑造,希望通过蕴含民族思想的戏曲艺术塑造理想中的现代国民。“戏曲虽游戏中事,颇具最大之魔力,恒有演仁人孝子之剧,令人可歌可泣而悲感交集者。”⑤
这一时期,随着近代西方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机制的传入,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开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接。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不仅出现了许多展览会、陈列馆,而且展出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戏剧资料。如1934年2月18日至20日在北平图书馆主办的戏曲音乐展览会:
所陈列戏曲撰著书籍北平图书馆所藏者计元杂戏及南戏十二种,其中十种为甲种善本;文人杂戏丛书八种,其中四种为甲种善本;明初杂剧九种,其中五种为甲种善本;万历崇祯间杂剧五十种,其中三十五种为甲种善本;明无名氏杂剧传奇十二种……⑥
北平国剧学会陈列馆中“以关于戏曲书籍为最多,中有清宫所藏剧本,并有奉旨修改者之原作,颇珍贵,图画陈列,各省戏台建筑照片约五十余幅,演剧所用切末图九十余种,戏台建筑图十二幅,皆注有说明。此外如民国以来堂会戏单全份,搜集颇不易。器具,有乐器十余种,戏圭一份,多外间不经见者……”“西面室内以戏曲旧照之陈列最为出色,中多名伶旧照,惜已逐渐褪色,恐难经久,整间所悬图画,如宋戏台式一种,武器图一百四十种,革属乐器五十九种”,此外还陈列有脸谱、身段谱、花名册等⑦。这些展览会、陈列馆中所展出的戏剧资料为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提供了极大便利。
20世纪30年代,延安文艺运动中对于戏剧的搜集、整理及创编并不止步于“发见”民众抑或“重塑国民”,而是将“劳动人民”提升为文艺实践的主体,以“民众”为主体内涵的“民间”理念也上升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原理⑧。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秧歌剧、河北梆子、花鼓戏等传统戏剧在创编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从形式上看,“从新旧梆子、秧歌、皮簧到话剧、歌剧;从快板剧、活报剧、幕表剧到熔新秧歌、新梆、新歌剧和话剧于一炉的‘四不象’,等等,不一而足”⑨;从内容上看,此时的戏剧演出多贴合时事,反映民众最为普遍的情感诉求,如《穷人乐》一剧在实际演出时采用传统戏曲用虚拟动作表现生活的“写意”手法。“他们自己拿着弯弯的镰刀,雁字排开表演收割场面,然后再动作麻利地表演扎麦个子,扛到场上”⑩,整场表演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实的美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时期“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样式与实践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⑪。1956年,民族识别与各民族历史调查活动为各地域、各民族传统戏剧文本及表演资料的搜集、整理及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9年,在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发出的《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规划》中提出编辑出版“四部集成”⑫,其中就包括《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此集成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梳理脉络,通过详实的资料图片多维度地呈现各省市戏曲音乐的真实样态,不仅有极为重要的资料学价值,还为今后类似书籍的编选标准、编选体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优秀范例。
20世纪80年代,对传统戏剧的挖掘与保护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特别是在非遗话语引入中国后,昆曲、京剧、豫剧、潮剧、越剧、粤剧、川剧、湘剧、晋剧等戏曲形式,弋阳腔、青阳腔、高腔、新昌调腔、宁海平调等声腔剧种及四平戏、蒲州戏、正字戏等民间小戏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戏剧”类别之中。所有这些都标示着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新时代”的到来。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然成为国家文化建设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重要内容。围绕着传统戏剧类非遗“表演”与“传承”问题的讨论,得以更加深入、全面、系统地展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全球性的文化政治策略,在理念上具有超越国家和民族、以追求人类共同性价值认同为目的的特点,同时它又强调文化的多样性,亦即文明的不同个性。”⑬正如有的学者提及,“民俗学核心(应)不再被认为是搜集整理来的定格资料。相反,它的意义和生机在于民众日常生活中如何不断被创造、表演和接受”⑭。这种立足于“日常生活”的保护发展在当下传统戏剧类非遗项目传承中,依然处于一种缺失状态。
传统戏剧类非遗中的“戏曲文化”“民俗文化”等样态并非静止且持续不变,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也应按照“其时、其地、其人”加以变化,而非在保护中一味追求“传统”。传统戏剧始终是以活态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其中的“物质”部分,如表演时的服饰、布景、道具、剧本,同戏曲的表演、声腔、脸谱绘制技法、乐器演奏等“非物质”部分相互转化、渗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艺术状态。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对戏曲“利用”方面的放松与失衡。在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中,第一,需要坚持回归生活的保护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归根结底是要保护对象在一地传统生活文化根基上原真性或原生性地(Authenticity)沿袭传承。”⑮就戏曲本质而言,其并非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种文化型的“生活相”或生活模式。如澳门地区的“神功戏”,其与“澳门的寺庙文化、民俗祭祀、民俗信仰等密切联系,并共同构成了具有文化认同性质的民俗活动载体”⑯;再如民众酬神演剧时的“戏曲”行为,伴随着民众祭祀、敬拜等民俗活动,共同构成综合性的文化景观,赋予文化以生生不息的活力。在非遗保护中,我们需要对“口头与行为、物质与非物质,有形和无形”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的整体空间——“生活场”有深刻认知,关注“鲜活的文化本体及其自主调适能力”,从而实现非遗向日常生活的回归,恢复其“在野”的能力。⑰
第二,需要坚持整体性保护原则。整体性包括生态整体性和文化整体性两层含义:生态整体性要求在保护单一剧种时,除了戏剧本身,还要综合考虑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对蕴含其中的民俗、音乐、舞蹈、服饰、道具等内容进行保护;文化整体性需要“对戏剧相关信息和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完整保护”⑱,从而实现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一原则的提出是由于文化的“复合性”,如“文化空间”,或称“文化场所”概念的提出,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集中国传统文学、文化、艺术之大成的传统戏剧类非遗,“在文化层面上不是呈平面状一维或二维物象,而是呈立体状的三维或多维物象,它不是静止、凝固与呆板的物理实体,而是自由、活泼、流动、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⑲。
第三,要践行参与式传播原则。“参与式传播是一个在各种机构、集体和人群之间的互动的、动态的、变化的对话过程”⑳。各种传播媒介成为开启对话的赋权工具,每个置身于生活中的个体都在通过“对话”构拟历史。如“非遗+电影”“非遗+动画”“非遗+短视频”等多种形式的出现,电影《白蛇传·情》将电影的“实”与戏曲的“虚”进行有效结合,融入现代科技,“在戏曲与电影、文戏与武戏、西方特技与东方审美之间达到了完美融合”㉑。传统戏剧类非遗项目的代际传承本身就是一个参与式传播的过程,“社会网络中的小媒介运作以及草根传播手段的运用”,其最终目的都是“通过回馈使民众被赋权行动”㉒。如岳阳市巴陵戏作为我国濒危剧种之一,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近年来,当地主要通过“传承基地建设”“剧目创作排演”“培育审美需求”等方式推动巴陵戏的生产性保护与传承,在尊重戏曲艺术自身规律的同时,与时俱进,“采用高科技、新媒介、探索新型管理模式”㉓,从而激发戏曲艺术的内在动力。
第四,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其相应文化区中的民众作为文化记忆缔造的参与者与践行者”㉔,是传承非遗文脉最具能动性的主体。伴随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的本土化实践,传统戏剧类非遗项目中的美学品格和文化精神得以挖掘和凸显。近年来,随着“非遗+旅游”模式的开发,戏曲艺术一时成为推动当地文旅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如山西省“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演艺·非遗进景区活动’、乡村文化记忆工程,大力发展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戏剧演出、乡村文化旅游、景区展演演出”㉕,带动地方旅游经济发展,促进传统戏剧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又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旅游开发中将衣、食、住、行等产业链融入戏曲主题公园的打造中,从文化景观建构、书籍出版、影音视频等多方面开发文创旅游新业态,推动传统戏剧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
此外,非遗传承人也在不断寻求更契合当下语境的“年轻化”表达,如在舞台表演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表现现代生活场景,提升观看体验;丰富“非遗+研学旅游”“非遗+主题公园”等模式的开发。传统戏剧类非遗研学旅游项目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特点,制订活动方案,如上海宛平剧院的“一日京剧研学营”,主要分为“寻·戏味”“感·京趣”“习·功法”“赏·国粹”“识·挚友”五个部分,让学生在一日之间,尽览国粹之美,在观摩和学习中感受京剧艺术的文化内涵,并在实践过程中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和思想上的共振。再如温州市瓯海区龙舟公园的文化景观建构,以“瓯海传戏”为主线,匠心设置“戏曲幻境+戏聚景山+戏游瓯海+戏象万千”场景,引导入园孩子分步探索“入戏、玩戏、探戏、知戏、赏戏”五个分支,成功打造沉浸式体验戏曲的儿童戏曲公园㉖。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过度的“市场化”与“馆舍化”会导致戏曲艺术本体的“隐形”,对文化符号的“重构”固然可以吸引市场目光,但在某些方面却与民众日常生活产生“割裂”,失去戏曲艺术赖以生存的“泥土气”,而变成一种看似高不可攀却丧失灵魂的“庙堂艺术”。此外,各地层出不穷的主题公园、文化街区、非遗研学活动等有“复制粘贴”之嫌,无法突出不同地域戏曲艺术的独特内涵,在非遗传承中忽视最基本的文化特性。
近年来,传统戏剧类非遗逐渐向着“资源化”“生活化”的方向发展,有论者提出讨论非遗价值的实现路径“在于是否能够激活非遗传承的内在活力”㉗。
围绕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注重“表演语境”的恢复,这也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早在1933年,李景汉和张世文编选的《定县秧歌选》㉘中就记录了秧歌的演出地点及“讲述者”㉙。20世纪80年代的“集成”工作更是进一步强调“仪式性和表演性作品”中的“讲述情境”:要在举行仪式与表演进行时搜集,直接了解其仪式的过程和演唱的具体情境。对有关仪式表演者,如巫师、师公、萨满、赞哈、阿訇、哭丧妇等,应进行多方面的观察与了解㉚。
这种对“表演者的年龄、性别、心境、忙闲、健康、爱好等诸种因素”和讲述情境的重视,实际上所关注的是个体生命本身的真实体验。这就要求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需要从现实生活状态出发,重塑和保持其赖以生存的民间“语境”,在生活化展演和馆舍化展览中使民众能够获得直接参与和体验的机会,而非将传统戏剧艺术束之高阁。如昆曲《浮生六记》的沉浸式实景演出,“复刻”了一个属于沈复、芸娘的戏中世界,观众在苏式园林的诗情画意中感受昆曲之美,传统戏剧的演出也在最大程度上运用了地方景观资源,突破单一演出形式,真正做到与观众的“双向互动”。但在这种艺术创新中也要注意“内容”与“形式”的有机融合,不能过度停留在视听层面,而是需要不断地打磨内容,挖掘文化深度,规避演出中的“雷同感”和形式内容“两张皮”的不良倾向㉛。值得一提的是,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中必须考虑到“表演语境”的现实意义。无论是脱离“表演语境”的传承人培养,还是看似繁花似锦、实则脱离民间土壤的种种非遗“展示”,都势必会丧失非遗的“活性”。因此,在传统戏剧类非遗的传承保护中,需要注重对相关文化资源的进一步挖掘,在完善传承体系的同时,关注传承人的自我认知及自我定位问题,强调戏剧表演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
其次,面对“线上民间”的出现,需借助融媒体技术,深度挖掘传统戏剧艺术气质与文化内涵,通过其中蕴含的音乐、舞蹈、文学等符号的转化与加工,对传统戏剧类非遗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多元化的展示。如越剧《新龙门客栈》以沉浸式表演空间的建构,推动了越剧艺术的当下发展,戏剧精神也在“传统”与“创新”的权衡中得以延续。再如北京皮影戏与动画《天官赐福》的联动、《黑神话·悟空》中的陕北说书、《原神》中的原创戏曲《神女劈观》等实践,将戏剧艺术与动画、游戏、影视等艺术表现形式进行结合,寻求表达和传递的“通途”。近年来,传统戏剧类非遗的“破圈”尝试为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互相理解及阐释开辟了道路,对蕴含其中的声腔唱词、民间传说、民俗信仰等文化元素进行“提炼”与“加工”,不仅增强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依恋与文化感知,还体现了传统戏剧类非遗丰厚的精神积淀和文化价值。
近年来,随着融媒体技术的发展,传统戏剧类非遗通过“互联网+”的传播模式、“虚拟性”的传承场域、多元立体的传承模式,推动了戏剧艺术传承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数字技术将各种文化遗产变成了‘比特’(bit),可以储存和编辑,传承载体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成为网上互动的数字图码信息,载体多样多元、形态丰富多样。”㉜一方面,可以通过不同传承主体,对各地域、各民族传统戏剧类非遗进行搜集、整理及建档,进一步加强数字技术的运用,对剧本、道具、脸谱、服装等知识遗产进行归类和划分,完善数据库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利用VR/AR、全息投影等技术,为观众打造身临其境的沉浸式空间。以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为载体,运用AI修复、沉浸式表演等数字技术进行赋能,并以优质内容创作与互动体验升级优化,从而实现传统戏剧类非遗传承发展的转型,在守正创新中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最后,要关注传统戏剧类非遗传承发展中的存续力问题。“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是否对校园文化建设有所助益,传统戏剧表演是否在年轻观众中受到欢迎,非遗布展是否多元立体地展现了传统戏剧的文化内涵。在积极探索传统戏剧类非遗发展路径的同时,也要敏锐地感知到在一片花团锦簇之下的传承“危机”。如在非遗的商业开发中,普遍存在重市场、轻文化的现象。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非遗保护与地方文化建设之间的密切关系,重视传统戏剧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及审美价值。
从根本上来说,传统戏剧类非遗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烙刻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是文化认同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练表达。在未来发展中,除了政府政策、资金的扶持外,还应借助大数据和云平台,依靠融媒体和互联网的技术力量,实现传统戏剧类非遗的广泛传播,在推进价值转化的同时,重视其“文化”属性的凸显,扩展对话、交流、互动的意义空间,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戏剧和中华文化魅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网络与数字时代增强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实现途径研究”(项目编号:18ZDA3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跨文化传播、数字媒体艺术传播、戏曲电影。